我如何轉變自己
 (感謝好友哲的分享)
(感謝好友哲的分享)
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小男孩,什麼也不懂的小男孩,根本不知道自己和一般人有什麼不同,我不喜歡和同年紀的男孩們玩在一起,反倒覺得和同年紀的女孩們相處非常愉快,我就這樣一直都和女生混在一起玩樂直到全家舉遷至新的小鎮定居,許多我的遠親像是表兄弟們也都住在那裡,那時大約是我剛升小學六年級和國中一年級的階段,在那小鎮上,因為我家族關係密切,我很快地就被這小鎮接納;我親戚中沒有表姐妹,但有許多表兄弟,他們也都是和我年紀相仿的小男生,國中一年級也正是男女開始分班的時候,正因為如此,我才有較多的機會和男生相處在一起;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比較喜歡和女生玩在一起,我講話的聲調輕柔細膩,對各項運動、汽車或騎馬打仗是絲毫不感興趣,我就像是花園中的雜草一般,無法和其他的花樹相稱。
在班上,我比其他同年紀的同學成熟較快,雖然我身體變壯了,可是我的行為舉止卻變得更女性化,也許是因為我把自己當成是女生,所以當時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班上的一些男同學開始對我逐漸成長的下體和陰毛感到好奇,偶而會對我全身上下摸索一番,對我而言,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可是誰知道,同班同學的好奇階段很快地就過去了,而我卻更沉溺其中的樂趣?和男生玩樂已成為我強烈的慾望。剛開始他們對我的好奇探索無關緊要,可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男孩們是非常聰明伶俐的,當我們逐漸成長,我們對性就更加的敏感注意;有一天,在班上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也是我的鄰居,叫我“queer”(譯註:queer是美國人稱呼同性戀者所使用較不好的字眼,有鄙視的意味;而較能被同性戀者接受的同意字是gay 或homosexual),那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揍人,當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queer”,只知道這是很不好的字眼,如果別人把我當成queer來看,我就不會受人喜愛;在當時的國中校園內,每一個人都想成為和別人“同類”的人,如此才能進入所謂的小集團或小圈圈內,我的好友稱我是queer,這表示我與眾不同,是一個homosexual,這也表示所有我的好友可能會因此棄我而去,這對我來說根本就是一場惡夢,我必須改變自己,改掉我女性化的行為,否則我就只有死路一條。
進入高中唸書後,我知道我必須對此事有所作為,但當時所知有限,我的樣子又像女孩子,更何況我以前的好友都已經叫我queer了,我又能如何。因此我對自己立下了幾項目標,我要學習成長,我要展現並証明自己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同時我也要隱藏我同性戀的傾向,直到這傾向完全消失為止;基於此,我開始著手進行以下工作;首先,我只和女生混在一起,至於男生,我則是避而遠之;接下來,雖然我不和男生接觸,可是我卻被他們的一切深深吸引,我知道這是非常冒險的;最後,我要學著開始和女孩子交往,並儘量在公開場合中親吻她們,但為了不讓男女性事過於頻繁,我決定加入教會成為一位基督徒,因為一位好的基督徒是不允許婚前有性關係的。
上體育課、自慰和父母親是我唸高中這段期間最大的挑戰,每一次當我接近一位全裸或半裸的男生,我的陰莖就會不由自主地勃起,無論我多麼努力地嘗試冷靜下來,它還是不聽使喚地挺立,因此上體育課時,我拒絕和男同學們一起淋浴或在他們面前換衣服,我更不可能下水游泳,我的體育老師和父母親用盡各種手段就是無法讓我改變心意,最後他們終於放棄了,我並不想告訴他們為什麼,我只是淡淡的說“即使我體育課的成績被當,我還是不會去上課的”;說真的,要不是我其它學科的成績表現優異,我的體育老師還真的會當我。
身為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對我的性傾向感到十分的內疚和自責,我常常祈禱上帝改變我,如果我自慰,我會更加的憎恨自己,因為我性幻想的對象總是男生,沒有女生;我自我反省並告訴自己,如果我不戒除自慰(一位小男生能做到嗎?),我又如何能克制其它的慾望呢?在學校或教堂裡,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偽君子,就像是住在一片漆黑的屋內,並透過既深且厚的窗子向外看屋外的世界,我感到非常寂寞,我只有全心全力投注學校課業,參加各項社團活動,並盡力讓自己表現完美無缺,我希望藉由我的完美表現,別人就會喜歡我,以彌補像我這樣一文不值的性變態。
我父親開始查覺到我的與眾不同,他非常害怕我就快要變成一個同性戀,因此他給我上了一課“男人應有的姿態”,他教我應該如何走路才像男人,帶我去打獵,叫我參加童子軍,並鼓勵我和女孩子發生性行為;有一天下午,我祖嬸嬸教我織毛衣,這可引來我祖母和父親的大聲斥責,他們罵她,說都是她把我變成同性戀,唉!他們總是互相怪罪;雖然我的怪異行為讓我家人難堪,但在家裡,沒有一個人願意提起有關“同性戀”的字眼,父親也不再去學校參加有關的懇親活動,因為他無法面對別人異樣的眼光對待,他以我為恥,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以生下像我這樣娘娘腔的兒子感到蒙羞。
在高中唸書這段期間,我那位最要好的朋友告訴其他同學我曾對他口交,他更向他們說我是“queer”,除此之外,在學校還有很多人,尤其是高我幾班的學長們,經常欺負和嘲弄我;有一次有好幾位學長集體逼我至角落,並用手拔我臉上的鬍鬚,他們更經常不斷地用髒話罵我,趁我獨自一人走在路上時追趕我,然後揍我一頓;還有一次上體育課時,一位同學在我夾克口裡偷偷放了女用衛生棉,就在我不知情下,衛生棉突然從我口袋裡掉出來,這引來大群圍觀的同學哄堂大笑;更有一次夜晚,不知是誰朝我丟了一塊磚頭,幸好磚頭沒打中我,反而是停在路邊車的玻璃窗受災殃;以上所發生的種種都深深地刺傷我的心,我感到極度無奈和悲傷,可是我還是繼續保持微笑,盡最大努力來贏取別人對我的友善對待;但是無論我多努力隱藏我的性傾向,多用心地想進入同學們的小圈圈,在學校裡,我還是不被同學們接納,雖然有很多女生很喜歡我(其實我從不瞪著她們的胸部看的),但是男同學不是憎恨我,就是根本不理我,他們認為我看起來很古怪、很好笑,還曾想試著改變我。
不用我多說,我當然很高興畢業並離開高中,在進入大學唸書後,我交了一位女友,教堂幾乎很成功地對我洗腦,身為一位基督徒,我想早日結婚並組成家庭,然而在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裡,一些年輕的男生或年長的男人,似乎可從我的外表看穿我的性傾向,他們開始向我展開攻勢,要我和他們做愛,當時我獨自一人背景離鄉,不受家人和教堂的約束,更不受認得我的人異樣眼光注視,雖然我並不想和他們發生關係,但我還是和他們做了,這就像是另一面的我從身體裡跳出來和這些人做愛,我根本就無法控制自己,我喜歡被愛撫、被珍寵和被玩弄,這感覺非常刺激又好玩,但這都是在隱密下做的。
就這樣在大學裡過了兩年,那時我還是很想結婚安定下來,我仍繼續和我女友交往,並開始和她發生性關係,我想先試看看和她做愛的感覺,以瞭解婚後我是否還能繼續這樣做,我雖然很愛我當時的女友,但這層愛的關係就好像她是我的好友或姊妹,她人長的漂亮,身材勻稱,活潑、有趣、又聰明,她對我很好,真的很好,她擁有所有最好的條件,如果世上真的有那麼一位女子能改變我,則非她莫屬了;我努力嘗試著親吻她,撫摸她的胸部,但我卻對這些愛撫覺得毫無樂趣可言;有一次,當我用手觸摸快到她的下體時,這種感覺就好像第一次我被強灌吞下很苦的藥丸,我知道我可以假裝很喜歡和她做愛,但是…喔,天呀,我真的很不喜歡,但我還是很努力試著做下去。
在大學裡,我也盡量避免和其他同性戀者相處在一起,我會避開那些樣子就像是同性戀的人,但有時我就是無法控制我的慾火,我的內心不斷大喊“不、不、不”,但我身體卻不聽使喚地朝向那些同性戀經常徘徊的暗巷裡走去,我們用眼光來互相傳達訊息,很快地就能夠搭上他們,喔!我真的很喜歡那種感覺,可是每當我發洩完了之後,留下的總是滿懷罪惡感,我很對不起我的女友,我又再一次挫敗了;我認為只要我能控制我身體的慾望,我和她之間的關係就還有救,可是事實上並不單純只有我的身體讓我陷入困境。
接下來,亨利,我的新室友進入了我的世界,對我來說,他是的我一項嚴格考驗,每晚我的身體都不斷向他吶喊,“每晚不斷地吶喊”,“每一夜晚”,終於在一夜晚,在我倆小酌一番後,我們發生關係了,我倆就這樣互相擁有對方直到清晨陽光升起;事情過後,我仍無法對他釋懷,我已深深地捲入這戀愛的漩渦──與一位男子,現在不再只是身體讓我陷入困境,還有心理;亨利不是同性戀者,他只是好奇嘗試而已,但我無法駕馭的激情幾乎把他逼瘋了,不得已他只好搬出去,我並不怪他,在認識亨利之前,我一直認為男人只不過是我性發洩的對象,和他們絕無所謂的愛情或婚姻關係,當時我也只認為一般男人就只能愛女人,但我錯了,我對亨利這樣的男子著了迷,我身體每一吋細胞都不斷地向他吶喊,但這次的感覺是我做對了。
我內心自省,如果我深愛這男人,我能留給我妻子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但我仍然無法接受我未來的日子就要如此地走下去的事實,我必須結婚生子,我必須選擇不公平對待的生活,我必須放棄我的性傾向,我必須在這同性戀的道路上獨自一人孤單地走下去,我怎麼能讓我的家人、女友和教堂失望呢?內心不斷地交錯掙扎逼的我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希望她能改變我的性傾向,可是在內心裡,我早已知道會得到的答案,我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同性戀者,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事實,上帝也無法改變,我的女友、心理醫生更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已受夠了這些內心的掙扎,一個人倒底要受苦受難多久才能接受真正的自己?究竟還要偽裝多久?要忍受多少罪惡感?失去多少尊嚴?承受多少自責、挫敗和絕望?忍受多少嘲笑和戲弄?還要受盡多少的擔心害怕被人發現?一艘獨自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小船,在暴風雨來襲前還能走多遠呢?就在我心理醫生可眺望碧草如蔭教堂中心的辦公室裡,我終於解脫了,我終於接受我是同性戀的事實,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我的人生就此光明重現,內心的掙扎也終於結束。
我愛我的女友,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也非常地愛我,但我還是必須告訴她事實,和她分手,我果我能愛一個男人就像我愛亨利那麼深,我就不需要女友,也不需要結婚,如果我和女友結婚,就等於毀了她的一生,她會心碎的。
接下來,我對母親坦然相告,我說“…你可以接受或拒絕我,這完全都在妳,我愛妳和父親,如果妳真的因此恨我或因為我讓妳們徹底失望而無法接受我,我會立刻轉身離開這裡(我家),在妳有生之年就不會再見到我。”
她回答“你是一個乖孩子,從不給我惹麻煩,你靠自己的毅力唸完大學,成績表現都是高人一等,我一直都以你為榮,現在你坦白告訴我你是同性戀,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總不能說我想抱孫子、我不希望你就這樣孤獨過一生或我該如何向別人解釋呢?等等這些話,你做你應該做的事,無論結果如何,我還是很愛你,我會設法為自己找出一條路走出來,但我必須警告你兩件事,第一,千萬別告訴你父親,第二,你必須知道今後你走的道路將是充滿崎嶇,如果一個同性戀走進酒吧喝酒,在他付帳走出去之後,老板會打破他剛用過的杯子,你知道這表示什麼嗎?”
我回答“我知道,我早就已經面對這事實了。”
我寧願去死也不願再憎恨自己和像是小偷般偷偷摸摸地隱藏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這樣地轉變自己,為自己找出一條路勇敢地走出來,一朵花的成長並不單純只是走上凋零,然後掉落至又濕、又冷、又黑暗的泥土裡腐爛而已;一朵花,無論是路邊的野花或只剩下沒幾片的花辦,或根本就是一株仙人掌,都會竭盡所能地在有生之年成長茁壯,當然最好是能在陽光下生長;在這世上,我無法改變我生下來就是一株蒲公英的事實,而剛好這時候玫瑰花是最受歡迎的,如果我無法讓自己變成玫瑰花,我就只得選擇接受自己不是玫瑰花的事實;而事實上,如果世人能接受我,我就能成為一株玫瑰花,如果我不能成為你家花園中的一株花,在這世上還有許多家的花園裡我能生長,我會移植我自己到上千個花園裡生長,無論有多麼艱苦難熬,我會繼續生存下來,直到找到一家擁有燦爛陽光的花園。
我母親在她臨終前還是將我的秘密告訴了家人,我的兄弟姊妹告訴我說,他們能夠接納我是一位同性戀,他們仍然會深愛我;但我父親卻不願再提起此事,並在我倆之間築起一座高牆,二十年過後,他得了絕症,在他去世前的一個月,他詢問我有關過同性戀生活的點點滴滴,就在那時我們之間的隔閡化解了,在最後的一個月裡,我們互相溝通,他去世時口中還不斷地叫著我的名字,真希望他能更早就叫著我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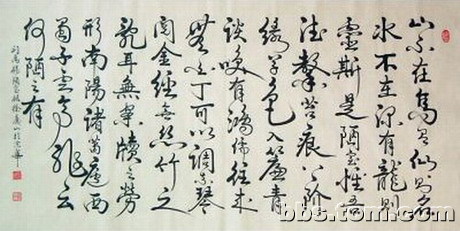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