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
 作者:李欣倫
作者:李欣倫
據說有些修行者會為了尋求感受而修行,企盼有光霧、神影的境界。
我只是初學者,神啟式的光暈未曾籠罩周身,不過坦白說,在禪修課程中,我也曾對奇妙光束充滿期待。那似乎成為一紙證明,證明心靈品質的提升,證明離苦難遠了點,離喜樂近了些。後來我逐漸明瞭,對這種境界的渴盼乃至執著,竟是人性最難割除的惡瘤。就像患者對健康的企求一般,純粹的健康究竟是何等模樣,我們不得而知。
平心而論,每個人多少都有些毛病,生理或心理的、顯見或幽微的病毒在大腦、身體植下種籽或蔓成雨林,若將所有的偏差與錯誤、反常及不自然都視為疾病,那麼,所有人都有病,都是病人。
當我練習觀察呼吸,才知道我病得很深。只要呼吸,只是呼吸。此時此刻,唯有氣息進出而無其它。起初,我想不過是觀察呼吸,應該很簡單,後來發現能持續而專注地觀察呼吸,絕對比完成一本幾十萬字的論文還難。這一秒、這一秒和這一秒,我專注呼吸,像觀察水流流動,但不知何時,我離開了呼吸(即使它仍在,但我已離開),遠足過去,漫遊未來,有關或無關的種種神思將我帶離當下,快樂、憤怒之事輾轉浮現,我在冷熱交替的回憶與妄想中,與情緒搏鬥。然後驚覺,呼吸在這,在這一秒,這一秒,這一秒,我又回到氣息河畔,凝視它貼著薄薄肌膚流動,流動,沒多久,我又擅自離開河畔,忽忽徜徉於尖塔、鐘樓、古堡、黑森林,或是廊廡、石階、燕尾脊。就像突然遠颺一般,我也隨時迫降於氣息河畔。
就這樣,我在蒲團上瘋狂地搬演著大遷移,這一秒我在,這一秒我仍在,這一秒我沒有離開,但當我再度意識到另一秒來臨之前,已遊歷了五大洲。《溪畔天問》的作者安妮‧狄勒德(Annie Dillard)曾引述一段話,表示人的當下感最多在二點三秒到十二秒之間。
學習觀呼吸後,我發現自己真正活在當下的時間少得可憐,大部分的時間裡,我沈湎過去,揣度未來,被巨大的不確定感緊緊擁抱。因此當我們嘲笑那些腦袋如水晶球、製造虛幻世界的瘋人時,別忘了自己也是他們的一員——連最簡單的呼吸都無法馴服的人,如何能稱得上多麼健康呢——我們不也在生產虛幻?
斗室裡、蒲團上沒有文字、乳房、耳語、眼神、氣味,唯有清楚的氣息之流和身體之島,但我們憑空創造了酒窩、金錢、權力,迅速折返於過去與未來,這難道不是瘋狂?當我們意識到這點,立即勃然大怒(我能掌握文字、金錢、女人及世界的種種複雜,卻無法掌握呼吸?)
然而,對呼吸發怒如同對喜馬拉雅山發怒一樣毫無意義,但我們仍不斷憤怒,站在真理面前耍孩子脾氣。想來有趣,我們常坐在定點揣想恐怖或虛擬的未來影像。明明坐在辦公桌前、躺臥床上或陷在柔軟的沙發裡,電視遙控器及零食就在手邊,優渥滋養著這一刻的肉體與精神,但奇妙的是,我們卻無故召喚顛倒夢想,任不存在的事實玩弄血壓、心跳及呼吸。
我很喜歡薩波斯基(Robert M.Sapolsky)在《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的論點,他說,斑馬或其餘動物所要擔心的往往是生存問題,例如飢餓、嚴重受傷或虎視眈眈的掠食者,牠們體內的壓力裝置幫助其渡過生存危機,身體也非常適應這種緊急需求,但現代人已經無須為了一頓晚餐而親自追獵與撲殺,沒有迫切的生存問題,卻將種種壓力於腦際搬演,薩波斯基幽默地說:「有多少河馬會擔心到牠們年老時,老人年金是否能夠發放?或是第一次約會時,該說什麼話?」在他看來,心理壓力是相當晚近的發明,「身為人,我們只要用想的,就能經歷強烈的情緒(同時引發身體劇烈的反應)。」
光是坐在沙發上,我們的身體就因為虛擬的壓力而啟動機制,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超時且頻繁地工作,但卻不是用來渡過現實中的危難,而是耗損在無意義的假想上,長久累積下來,對抗壓力的系統逐漸失靈,很難不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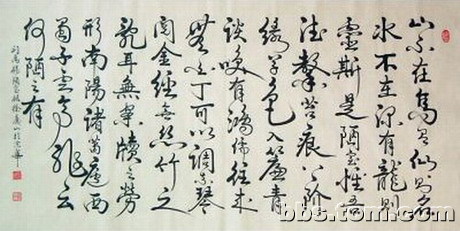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