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的意義
 有人問睦州大師:我們每天要穿衣服、吃飯——怎樣才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
有人問睦州大師:我們每天要穿衣服、吃飯——怎樣才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
睦州回答說:我們穿衣服、我們吃飯。
問的人說:我不明白。
睦州答道:如果你不明白,那麼就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飯。
禪是什麼?禪是一種非凡的成長。由於包含了很多危險,所以禪的這種可能性極少成為現實。曾經有很多次,這個可能性存在過——某種靈性事件本來應該成長成為像禪一樣的東西,但是它從來沒有達到過它的極致。只有一次,在人類意識的歷史上出現過像禪一樣的東西。禪是很罕見的。所以首先我要讓你們明白禪是什麼,因為除非你們懂得,否則這些禪的故事對你們不會有所幫助。你需要知道完整的背景。在那個背景中、在那個來龍去脈中,這些故事會變得明白易懂——你會突然把握它們的意思和意義,否則它們的這些意思和意義是支離破碎的。你可以欣賞它們,有時候你可以嘲笑它們;它們富有詩意,它們本身是美麗而獨特的藝術品,但是僅僅看這些故事,你將不能看透禪的意義。
所以首先試著跟著我慢慢看透禪的成長——它是如何發生的。禪在印度出生,在中國成長,而在日本開花。整個情況是罕見的。為什麼它在印度出生卻不能在這兒成長而不得不尋求另一片土壤?它在中國長成大樹,卻又不能在那兒開花,它不得不又一次尋求一種新氣候,一種不同的氣候——然後在日本它象一棵櫻花樹一樣開放出成千上萬的花朵。這不是巧合的,這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沉的內在的歷史。我要向你們揭示它。
印度是個內向型的國家,日本是個外向型的國家,而中國正處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印度和日本是絕對的對立面。那麼種子怎麼會在印度出生而在日本開花呢?它們是對立的,它們沒有相似的點;它們是矛盾的。還有,為什麼中國正好處在中間,給它提供了土壤?
種子是內向的。試著去理解種子的現象,理解種子是什麼。種子是不向外伸展的;種子其實是轉向自身的。種子是內向的現象,它是內心的——它的能量是向內移動的。那就是為什麼它是一棵種子,一棵包裹著的、封閉著的、完完全全脫離於外在世界的種子。事實上,種子是世界上最寂寞、最孤立的東西。它在土壤中沒有根基,在天空中沒有枝葉;它和大地沒有聯繫,和天空沒有聯繫。實際上它與四周沒有關係,種子完全是一座島嶼,一座孤立而內陷的島嶼。它不與其他東西牽連。它的四周包裹著一層硬殼,它沒有窗,沒有門;它走不出來,也沒有東西進得去。
種子對印度來說是很自然的。印度的精神能夠創造出有生命力的種子,但不能夠給它們提供土壤。印度是一種內向型的意識。
印度說外在世界並不存在,即便它存在,它也是由構成夢境的相同材料作成的。印度的整個精神就是在試圖發現怎樣逃脫外在的世界,怎樣進入心靈的內在洞穴,怎樣歸於自己的中心,怎樣才能認識到存在於外在意識的整個世界只不過是一場夢——最好的也不過是一個美夢,最差的也不過是一場惡夢;不管美夢還是惡夢,就其實而言,它是一場夢,人不應該太在乎它。人應該覺醒,並且忘掉這外在世界的整個的夢。
佛陀,摩坷毗羅,梯洛帕(Tilopa),喬羅迦陀,迦比爾的整個努力,努力,他們的這個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努力,始終就是怎樣擺脫生死輪回:怎樣封閉你自己,怎樣完全斬斷你的一切關係,怎樣變得獨自一人、超然於世,怎樣向內走而忘掉外在。那就是禪誕生在印度的原因。
禪的意想是dhyan。Zen是dhyan的日語變音。Dhyan是印度意識的整個努力。Dhyan意味著極其孤單、極其沉浸於你自身的存在,以至於連一點簡單的思想都不存在。實際上,在英語裏沒有直接對應的譯名。Contemplation不是準確的譯名。Contemplation的意思是思想、反思。甚至連meditation也不是準確的譯名,因為meditation(冥想)涉及到一個冥想的客體;它意味著有某些東西在那兒。你可以冥想基督,或者你可以冥想十字架。可是dhyan意味著極其孤單以至於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被冥想。沒有客體,只有單純的主體存在——一片沒有雲彩的意識,一片純淨的天空。
當dhyan這個字傳到中國時,它變成了chan(禪)。當chan到達日本時,它變成了Zen。它們來源於同一個梵語dhyan。
印度能夠孕育出dhyan。數千年來,整個印度意識都走在Dhyan的道路上——怎樣去掉一切思想,怎樣紮根於純淨的意識之中。伴隨著佛陀,這棵種子誕生了。以前很多次,在釋迦牟尼以前,這棵種子就存在過,但是因為它不能找到合適的土壤而消失了。如果把這樣的種子給予印度意識,那麼它將消失,因為印度意識是越來越向內移動的,這棵種子會越變越小,越變越小,越變越小,直到有一個時刻,它變成了無形的,一種向心力使東西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原子——直到突然間它們消失了。在釋迦牟尼以前,有很多次,這棵種子誕生過——釋迦牟尼不是第一個精心、然後成為一個禪者(dhyanri)——一個偉大的靜心者的。實際上,他是一長系列中的最後一個。他自己記得他以前有24個佛。另外還有24個耆那教的替沙克,他們都是靜心者。他們不做別的,他們只是靜心,靜心,靜心,直到一點,在那兒唯有他們存在,別的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種子伴隨著帕拉斯那特(Parasnath),伴隨著摩坷吡羅,尼米那特(Neminath),以及其他人誕生過,然而它留在印度意識中,印度意識能夠孕育出種子卻不能夠成為它合適的土壤。它向同一個方向不停地運動,那麼種子就會變得越來越小,象分子、原子,直到消失。那就是在《奧義書》那兒所發生的;那就是在《呋陀經》那兒所發生的;那就是在摩坷吡羅以及所有其他人那兒所發生的。
在佛陀那兒,它也即將發生。菩提達摩救了他。如果這棵種子留在印度意識中,它也將融化。它將不會發芽,因為發芽必須要有另一種土壤——一種平衡的土壤。內向性是一種很強的不平衡,它是一個極端。
菩提達摩攜帶著種子逃到了中國。在意識的歷史上,他做了一件最偉大的事:他為佛陀帶給世界的種子找到了一片合適的土壤。
據說佛陀親口說過:我的宗教的存在不會超過500年,然後它會消逝。他知道它總是那樣發生的。印度意識會連續地擠壓它,使它變成越來越小的碎片,然後有一個片刻會來臨,它變得太小以至於看不見了,它完全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它消失在天空裏。
菩提達摩的實驗是了不起的。他看遍世界,為了找到一個這棵種子可以成長的地方而深入地觀察。
中國是一個很平衡的國家,既不象印度,也不象日本。金色的中庸是那兒的道路。儒家提倡走中庸之道:既不內向,也不外向;既不對這個世界想得太多,也不對那個世界想得太多——正好維持在中間。中國沒有孕育出宗教,只孕育出了道德倫理,沒有宗教在那兒誕生。中國意識不能夠孕育宗教。它不能夠創造出種子。所有存在於中國的宗教都是進口的,他們都來自於外界。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它們都來自於外界。中國是一片好土壤,但是它不能夠創始任何宗教,因為要創始一個宗教,它必須移向內在世界。要孕育一個宗教,它必須像女性的身體一樣,像子宮一樣。
陰性意識是極其內向的。一個女人生活在她自己裏面;圍繞著她的,是一個非常小的世界,盡其可能的小。那就是為什麼你不可能讓女人對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感興趣。不能。你不可能和她談論越南,她不會操這份心。越南太遠了,太外面了。和她息息相關的是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孩子,狗,傢俱,收音機,電視機。包圍著她的是一個非常小的世界,只是一個最小的世界。由於女人的周圍沒有很大的世界,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間很難進行理智的談話——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一個女人只有在保持沈默時才是美麗的;一旦她開始談話,愚蠢的東西就會從她裏面冒出來。她不能夠是太哲學性的。不,那不可能。這些東西太遙遠了,她不會去操這個心。她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的小圈子裏,她是那個中心。任何有意義的事物只有在和她有關時才有意義——否則它就是毫無意義的。她搞不懂你為什麼那麼關心越南。你出什麼毛病了?你和那些越南人根本一點兒關係也沒有。不管是不是在進行戰爭,它和你毫無關係。孩子病了,而你卻在關心什麼越南!她簡直不能相信當她在你的身邊時,而你卻在讀報紙。
女人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女人是向心的、內向的。所有女人都是印度人——無論她們住在哪兒,都沒有關係。男人是離心的,他向外走。男人一旦能找到一個藉口,他就會逃離家庭。只有在他無處可去時,他才會回家;當所有的俱樂部、旅館都關門了,那麼,還能幹什麼呢?他就回家。沒地方可去了,他才回家。
一個女人總是以家為中心的,以家為基地的。只有在絕對必須、萬不得已時,她才出去。當它成為絕對的必需時,她才出去。要不然她就以家為根據地。
男人是流浪漢,遊蕩者。整個家庭生活是由女人,而不是由男人創造出來的。事實上,文明的存在是由於女人而不是由於男人。如果允許,男人會成為遊蕩者——沒有家,沒有文明。男人是向外走的,女人是向內走的;男人是外向型的,女人是內向型的。男人總是對自身以外的東西感興趣,那就是為什麼他看上去更健康一些。因為當你太關心你自己時,你會病的。男人看上去更樂呵呵。
你會常常發現女人很悲傷並且太關心自己。一點點頭疼,她們就會大驚小怪,因為她們生活在裏邊——這個頭疼就會變成一件很大的事,失去了平衡。但是一個男人會把這個頭疼忘得一乾二淨,他有太多別的頭疼的事。在他的周圍,他創造了太多的頭疼,所以他不可能發現自己的頭疼並且把它當回事兒。它太微乎其微了,他能忘掉它。一個女人總是會提心吊膽——一會兒腿有問題,一會兒手有問題,一會兒背有問題,一會兒胃有問題,老是有問題——因為她的自我意識是向內聚焦的。男人沒有女人這麼疾病纏身,男人更健康,更向外,更關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
那就是為什麼,在所有宗教裏,你會發現在有5個人在場的情況下,其中4個必定是女人,剩下1個人是男人。而且男人之所以來可能僅僅是因為某個女人的緣故——太太要去廟裏,所以他只好跟著她一起去。或者,她要去聽關於宗教的談話,所以他和她一起來。在所有的教堂裏,都是這個比例。所有的教堂、寺廟,無論你去哪里。甚至在佛陀那兒也是這個比例,在摩坷吡羅那兒也是這個比例。佛陀那兒有5萬桑雅生——其中4萬是女人,1萬是男人。為什麼?
從肉體上來說,男人可以變得更健康,從精神上來說,女人可以變得更健康,因為他們關注事是不一樣的。當你關注他人的時候,你就能忘掉你自己的身體,你就能在肉體上變得更健康,然而從宗教上來說,你不可能這麼容易地成長起來。宗教的成長需要內在的關注。一個女人非常容易成長從而進入宗教,那條道路對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但是要她在政治上成長倒是難上加難的。內向型有內向型的好處,外向型有外向型的好處——兩者也各有各的隱患。
印度是一個內向型的、陰性的國家;它象一個子宮,富有接受性。但是如果一個孩子永遠留在子宮裏的話,這個子宮將轉化成一座墳墓。孩子必須從母親的子宮出來,否則母親就會把孩子扼殺在裏面。他不得不逃離,從而找到外面的世界,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子官可能是很舒服的——確實如此!科學家說至今為止我們尚未能夠創造出比子官更舒服的東西。科學如此發達,我們竟然還不能創造出更舒服的東西。子宮簡直就是一座天堂。然而連孩子也不得不離開這座天堂,從母體中出來。超過一段時間,母體就會變得很危險。子官能夠扼殺生命,因為她將成為一座監獄——在一段時期內它是有益的,就是當種子在成長時,它是有益的。但是接著,種子就應該被移植到外面的世界來。
菩提達摩環顧了周圍,觀察了整個世界後,發現中國是一塊最好的土壤,它正好是一片中庸的土地,一點也不極端。氣候沒有極端,所以樹木可以容易地生長。中國擁有非常平衡的民眾。平衡正是讓事物成長的合適的土壤;太冷了不好,太熱了也不好。在-個平衡的氣候中,既不太冷也不太熱,樹木就能夠生長。
菩提達摩帶著種子逃走了,攜帶著印度所創造的一切。沒有人覺知到他在做什麼,但這是一項偉大的實驗。結果證明他是對的。在中國,這棵樹長成了,長成了參天大樹。
然而,儘管這棵樹越長越巨大,卻不開花。花朵沒有到來,因為花朵需要外向型的國家。正如種子是內向的,花朵是外向的。種子向內移動,而花朵向外移動。種子好象陰性意識,花朵好象陽性意識。花朵向外在的世界開放,向外面的世界散發芳香。隨後,芳香乘著風的翅膀,到達天涯海角。向著所有的方向,花朵釋放著包容在種子裏的能量。它是一扇門。花朵願意變成蝴蝶而飛離大樹。事實上,那就是它們以一種巧妙的方式正在做的事。它們正在釋放樹的精華,那正是樹對於這個世界的意義和重要性。它們是非常偉大的分享者。種子是個十足的吝嗇鬼,它局限於自己,而花朵是個揮霍者。
日本是為花朵所需要的。日木是個外向型的國家。它的生活方式和意識風格是外向型的。瞧……在印度,沒有人太在意外面的世界;衣服、房子、生活方式。沒有人在乎。那就是為什麼印度仍然這麼窮。如果你不為外在世界擔憂,你怎麼可能變得富裕呢?如果不去關心如何改善外在世界,你就會繼續窮下去。印度一直很嚴肅、一直準備逃離生活,那些佛們談論的儘是如何從存在本身出來變成完全的出世者——而不僅僅是從社會那裏出來成為完全的出世者,徹底的出世者是從存在本身超脫出來!存在太無聊了。用印度的眼光來看,生活僅僅是灰色的——在它裏面,沒有有趣的東西,一切都很無聊,都是負擔。因為過去的業障,人不得不總是背負著它們。即使一個印度人墮入情網,他也說這是因為過去的業障才必須經歷它。連愛情也似乎是人不得不拖著的一個負擔。
印度傾向於死亡似乎更甚於生命。一個內向型的人必定傾向於死亡。那就是為什麼印度發展出了所有的如何死得完美徹底的技巧,如何死得完美徹底,以至於你就不會再被生出來。死亡成了目標,而不是生命。生命是為愚昧的人準備的,死亡是為智慧的人準備的。不管一個佛,一個摩訶毗羅有多麼美好,你都會發現他們是封閉的;他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漠然的氣息。不管正在發生什麼,他們都無動於衷。不管是以這種方式還是那種方式發生,都沒關係;不管世界將繼續存在還是滅亡,都沒關係……一種令人歎為觀止的漠然。在這種漠然中,開花是不可能的;在這種自我禁閉的狀態下,開花是不可能的。
日本則是截然相反的。在日本的意識中,內在似乎是不存在的,只有外在是有意義的。看—看日本人的服裝。儘是鮮花與彩虹的色彩——似乎外在是非常有意義的。看一看印度人古代的服裝,再看一看日本人的。看看印度人吃飯時是什麼樣的,再看一看日本人。看一看印度人喝茶時是什麼樣的,再看一看日本人。
日本人把每件簡單的事都創造成—項慶祝。喝茶,他使它成為慶祝。喝茶變成一種藝術。外在十分重要,服裝十分重要,關係十分重要。你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出比日本人更外向的人——他們總是保持微笑和愉快。在印度人看來,他們顯得淺薄,他們看上去不嚴肅。印度人是內向型的民族,日本人是外向型的。他們是相反的。
日本人總是在社會上活動。整個日本文化關注的是如何創造一個美麗的社會,如何創造美好的關係——在每—件事情上,在每一件微小的事情上——如何賦予它們意義。他們的房於太漂亮了。連一個窮人的房子也有它自身的美;它是藝術的,它具有它的獨到之處。它可能並不富麗堂皇,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富麗堂皇的——由於它的美、它的精心安排,以及花費在每一個微小的細節上的心思:窗該在哪兒,該用哪種窗簾,怎樣由窗戶、或者從哪兒將月亮請入房內。這些都是很微小的事,但每個細節都是重要的。
對於印度人,什麼都不重要。如果你去一個印度的寺廟,它連一扇窗戶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沒有衛生設備,沒有考慮空氣,沒有通風裝置——一無所有。甚至寺廟的前面,你會發現牛趴著,狗在打架,而人們在祈禱,誰也不在乎。他們對外在沒有感覺,他們對外在無動於衷。
日本則非常注意外在——正好處於另一極端。日本是個合適的國家。而後,禪的整棵大樹移植進了日本,在那兒它開花了,絢麗多彩。它開花了。
這就是又一次要發生的事。我又在談論禪。它不得不回到印度來,因為那棵樹開花了,花兒凋謝了,而日本人不能夠創造種子。日本不能夠創造種子,因為它不是一個內向型的國家。所以,所有的一切現在都變成了外在的儀式。禪在日本死了。過去它確實曾經開過花,然而現在,如果看書的話——讀鈴木大拙及其他一些人的書——如果你去日本尋找禪,你會兩手空空地回來。現在禪在日本已經消失了。那個國家能夠幫助它開花,但現在花兒卻消失了,飄落到了地上,那兒不再有什麼東西。那兒有的是儀式——日本人是很儀式化的——例行儀式存留著。禪寺裏的一切都按老規矩繼續著,似乎內在的精神還在那兒,但是內在的神殿空空如也。房子的主人已經搬走了。在那兒神不再存在——只有空洞的儀式。他們是外向型的民族,他們會讓儀式繼續下去。每天早上他們將在5點鐘起床——那時會有一記鑼聲——他們將走到茶室,他們將喝茶;他們將走到他們的禪房,他們將閉著眼睛坐著。一切都循規蹈矩,好象精神仍然存在,然而實際上它已經消失了。寺廟在那兒,成千上萬的和尚在那兒,然兒樹已經開過了花,種子不可能在那兒產生。
因此我在這兒談了這麼多關於禪的話——因為又一次,只有印度能夠創造這棵種子。整個世界存在於一種深刻的統一與和諧中——在印度,種子能夠又一次被孕育出來。然而現在世界上很多事都變了。中國不再具有可能性,因為它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外向型的國家,它成了共產主義的國家:現在,物質比精神重要。現在,由於新的意識波動,它封閉了自己。
我認為,如果將來還有一個國家可能成為那片土壤的話,那就是英國。
你一定會吃驚,因為你可能覺得它將是美國。不是。現在世界上最平衡的國家是英國,正如在古代是中國。種子必須帶到英國,種在那裏;它不會在那裏開花,但是它會長成一棵大樹。英國意識——保守而恪守中庸,自由而絕不走向極端,正好停留在中間——將是很有用的。那就是為什麼我允許越來越多的英國人來到我身邊。這不僅僅是簽證的緣故!因為,一旦種子準備好了,我希望他們會把它帶到英國。從英國,它會到達美國,它將在那兒開花,因為美國目前是最外向型的國家。
我告訴你們禪是很罕見的現象,因為只有當所有這些條件都滿足時,這樣的事才會發生。
現在,試著理解這個故事。這些小趣聞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懂禪的人都說:來自你存在深處的東西都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通過創造一種情景,能夠暗示它。詞語根本無法說明它,一則生動活潑的趣聞卻能夠。那就是為什麼禪是這麼注重趣聞。它在寓言裏存活,在寓言裏暗示,沒有其他人能夠創造出這麼美麗的寓言。有蘇非派的故事,有哈西德派的故事,還有一些別的故事,但沒有一個能與禪的故事媲美。禪擁有切中要害的訣竅,它能夠暗示難以暗示的東西。而這樣簡單的方式,你可能會錯過它:你必須去尋找它,你必須去摸索它,因為趣聞本身是這樣的簡單,以至於你會錯過它。它不太複雜,實際上,頭腦是不需要的;恰恰倒是,心需要敞開,這樣,你就會讀懂它。
看,這則短小的趣聞透露了禪的整個意義:
有人問睦州大師:我們每天要穿衣服、吃飯——怎樣才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
要是他拿同樣的問題去問佛陀的話,他會得到不同的答案。那個答案將來自一個「種子頭腦」。佛陀將說:一切都是虛幻的——吃飯,穿衣,一切都是虛幻的。要變得更加覺知。要看到世界的虛無性和夢幻性。一切都是摩耶(maya,幻象)。要變得更加覺知,不要試著去尋找怎樣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因為一個人怎麼能夠從夢境中解脫出來呢?一個人只要變得覺知,他就出來了。你見到過從夢境中解脫出來的人嗎?夢境是不真實的,你怎麼能從中解脫出來呢?不可思議的是,你首先進入了它!現在你又在自找麻煩,詢問如何從那兒解脫出來。你是怎麼樣進入夢境的?就是憑著你相信它是真實的。那就是為什麼人會進入夢境——相信它是真實的。所以,你只要放棄你所相信的,看到它是不真實的,那麼你就從夢境中出來了。要出來是沒有什麼步驟的,也沒有什麼技巧和方法。佛陀一定會說:瞧……不的整個生命是一場夢——然後你就解脫出來了。]
要是去問中國的天才孔子——他具備平衡的頭腦,既不外向,也不內向——他將會說:沒必要從中解脫出來。遵循某些規則,你將能夠享受這些東西。孔子會給出一些規則;而那些規則必須遵循,這就夠了。人不需要解脫出來。一個人只要合理地安排他的生活就行了。這個人甚至應該合理地安排他的夢境的生活。孔子說,即使在你的夢中你也會做錯事,你必須反省——在你醒著的時候,你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否則你怎麼會在夢中犯出錯呢?安排好某些事,平衡好某些事——那就是為什麼他有3300條規則。
但是如果在日本,一定會有截然不同的回答:佛陀的回答來源於種子,孔子的回答來源於樹木——睦州的回答則來源於花朵。當然這些都紮根於同一真理的不同的回答,但他們沒有使用同樣的象徵,他們不能。睦州所說的正象花朵,這是最完美的可能性。
睦州回答說:我們穿衣服,我們吃飯。
如此簡單的一個回答——有十分的可能你會錯過它。你可能會想:他在說什麼?看上去它好象是廢話、胡話。那個人問:我們每天要穿衣服、吃飯——怎樣才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而睦州回答:「我們穿衣服,我們吃飯。」
睦州在說什麼?他在暗示什麼?這是一個巧妙的暗示。他說的是:我們也這樣做——我們吃飯,我們穿衣服——但是我們是那麼全然地吃,以至於吃的人不存在了,只有吃存在。我們是那麼全然地穿,以至於穿的人不存在了,只有穿存在。我們走路,但沒有走路的人,只有走存在。所以是誰在要求從中解脫出來?
看一看這巨大的差別吧。佛陀會說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夢,你的吃、你的穿、你的走——而睦州說你是一個夢。天壤之別。睦州說的是:不要把你自己帶進去,儘管吃飯、走路、睡覺好了。是誰在要求從中解脫出來?丟掉這個自我;它是不存在的,當你不存在時,你怎麼可能從中解脫出來?並不是走路是一個夢,恰恰是走的人是一個夢。
.
仔細地觀察——如果你真在走,其中有沒有什麼走的人?走發生,它是一個過程。雙腿移動,雙手移動,你呼吸得更多,風迎面吹來,你享受;你走得越快,你就越感到有活力——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真的有一個走的人嗎?有沒有一個人坐在其中,還是僅僅是這個過程存在?如果你變得覺知,你會發現只有過程存在。自我是幻象:它僅僅是頭腦的產物。你吃,你會想一定有個吃的人存在,因為邏輯說:假如沒有一個走的人在裏面,你怎麼可能走?假如沒有一個吃的人存在,你怎麼可能吃?假如沒有一個愛的人在裏面,你怎麼可能愛?這是邏輯所說的。可是如果你愛過的話,如果你達到過愛真正存在的那一個片刻,你一定知道沒有愛的人在裏面——只有愛,只有一個過程,一股能量。沒有人在裏面。
你靜心,然而有沒有靜心者存在?當靜心達到開花,一切思維停止時,誰還在裏面?有沒有一個說一切思維都停止的人存在?如果存在,那麼這個靜心還沒有開花;至少還有一個念頭在那兒。當靜心開花時,根本沒有人記錄它,根本沒有人確認它,根本沒有人說:是了,它發生了。你說:是了,它發生了的那一片刻——它就早已丟失了。
真正的靜心,寧靜籠罩一切;極樂無拘無束地悸動著,和諧無邊無際地彌漫著,然而沒有人記錄這一切。沒有人說:是了,這發生了。那就是為什麼《奧義書》說,當一個人說「我證悟到了」時,你可以肯定地知道他還沒有。那就是為什麼所有的佛都說,無論何時當一個人聲明,那聲明本身就顯示出他還沒有到達最高峰,因為在最高峰,聲明者消失了。事實上,它從來就不存在。吃不是一個夢——吃的人才是夢。整個重點,從種子移向了花朵。
那就是為什麼很多西方人認為把「禪宗」叫作「禪的宗教」是不合適的,因為在那些答案中他們看出了巨大的差別。但是他們錯了。「禪的佛教」是徹徹底底的純粹的佛教,甚至它淨化了佛,淨化了佛教概念。它是精華之精華,是最純淨的禪定(dhyan),是意識最純淨的開花。沒有任何中心,你存在著。沒有任何人,你存在著。你存在,但是同時你不存在。那就是梯洛帕所強調的:無我(noself),無己(anatta),空(emptiness),無(void)。
睦州在說什麼?他說:「我們穿衣服、我們吃飯。」他的答案結束了。他的答案完美無缺。他說的很簡單:我們吃,我們穿,我們從來沒發現有什麼問題,我們從來沒發現能夠從中解脫出來的人。裏面沒有人存在。吃存在,穿存在,自我不存在。
他是在說:不要問愚蠢的問題。問的人說:我不明白。他來的目的可能是想找到一些規則和律條,怎樣成為一個宗教的人,怎樣丟掉這些吃飯穿衣的瑣碎之事,千篇一律的例行之事。每天,一次又一次,一個人不停地做著同樣的事。他一定覺得厭倦無聊了。每個人都會到達這一點。如果你有點兒聰明的話,你會到達感到無聊的這一點。只有蠢人和聖人才從來不會感到無聊,相反,聰明的人一定會感到厭倦。怎麼回事?每天你睡覺,只是為了早上又一次起床。然後吃早飯,然後上班,然後這個,然後那個。你知道你做這一切,就是為了又一次睡覺,你知道得很清楚,早上,同樣的事又要開始重演。人開始覺得自己像機器人。
如果你覺知到,正如古代印度人所覺知的,這樣的事已經持續了幾百萬世了,那麼,你必定會感到無聊透頂。那就是為什麼他們說:如何從中解脫出來?這個生死輪回持續著,磨呀,磨呀,磨呀,正象一張破損的留聲機唱片,不停地重複同一條音槽。在你身上,這已經發生了幾百萬次。你戀愛,你結婚,你努力工作,你生孩子,你奮鬥,你死亡。一次又一次,它重複到令人幾乎作嘔。那就是為什麼,當覺知到這個反反復複的再生現象時,印度感到了無聊;整個意識感到極其厭倦,因而整個努力變成了「如何從中解脫出來?」那正是那個人來要求睦州做的:幫助我解脫出來。它太厲害了,我不知道從哪兒逃脫。每天要穿衣吃飯——怎樣才可以從這死氣沈沈的常規中解脫出來?睦州說:我們穿,我們吃。
他說了很多東西。他說沒有什麼要解脫的人,因此,如果沒有人的話,你怎麼會感到無聊?是誰在感到無聊?
我也是每天早上起床,洗澡,吃飯,穿衣,做一切你所做的。但是我不感到無聊,我可以一直這樣做,直到永恆的終點。為什麼我不感到無聊?因為我並不存在,所以誰會感到無聊呢?同樣,如果你不存在,誰會說這一切是重複?每個早晨是新的,它不是過去的重複。每頓早餐是新的、每個時刻都象清晨草尖上的露珠一樣新鮮。正是由於你的記憶——收集過去,背負過去,一直透過佈滿灰塵的過去來看待新鮮的時刻,你才感到無聊。
睦州生活在當下,而不把其他時刻拿來與它相比。沒有一個背負著過去的人,也沒有一個思考著未來的人。只有一個生命的過程,一條意識的河流,不停地從這一片刻流向下一片刻,總是從已知的流向未知的,總是從熟悉的流向不熟悉的。因此是誰在那兒煩惱要從中解脫出來呢?沒有人。睦州說:我們吃,我們穿。這就夠了!我們不在其中製造問題。
問題的產生是因為心理記憶。你總是帶進你的過去。你總是把它帶進來,比較、判斷和抱怨。如果我給你看一朵花,你不是直接地看它,你說:是的,這是一朵美麗的玫瑰。有什麼必要要把它叫作玫瑰呢?你把它叫作玫瑰的那一個片刻,你已經把它和別的花作比較,你辨明瞭它的身份,你把它歸了類。你把它叫作玫瑰的那一個片刻,你稱它美麗的那一個片刻,你的所有的美的概念、玫瑰的記憶、相象,以及一切的一切,都進來了。玫瑰迷失在群體中。這朵美麗的花迷失在你的記憶、相象和概念中。接著,你會感到厭倦,因為它和別的玫瑰看上去差不多。
區別是什麼?如果你能夠直接地看這個現象,看這朵玫瑰,眼光新奇而沒有過去,意識純淨而知覺清晰,門戶打開而不用語詞,如果你能夠在此時此地和花朵呆上一會兒,那麼你就會理解睦州的話:「我們穿衣服、我們吃飯。」他是在說完全當下地做一切事。那麼你就不會感到它是重複的。因為你不在那兒,那麼誰來背負過去,誰來設想未來?你不存在,然後,存在的另一種品質就會發生在你身上——時時刻刻都是新的,流動的,放鬆的,自然的。從這一個片刻到另一個片刻,人只是輕輕滑過,就象一條蛇有時從舊皮中蛻出來一樣。舊皮留在了身後,他從不向後看;他不準備帶著舊皮。一個覺知的人只是從一個片刻滑入另一個片刻,正象一滴露珠從草葉上滑過,一無牽掛。一個覺知的人沒有負擔,他輕裝而行。然後一切都是新的,沒有問題被創造出來。
睦州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創造問題,因為我們從來不知道有誰可以解決問題。問題一旦被創造出來,就不能解決。不要創造它們,這是解決它們的唯一辦法。因為一旦創造,就在這個創造中,你就已經邁錯了一步。然後,無論你做什麼,那邁錯的一步都不會允許你解決它。如果你詢問如何丟掉自我,你就已經創造了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有成千上萬的教師不停地教你如何解決它,如何變成謙虛的人,如何不做一個自我中心的人。什麼也沒發生——即使在你的謙卑中,你仍然以自我為中心;即使在你的無我狀態中,你還是帶著一個微妙的自我。不。那些有知識的人將不能幫你解決任何問題。他們只會問自我在哪兒。他們只會問問題到底在哪兒。他們會幫你理解問題,而不是解決它,因為問題是虛假的。如果問題是錯的,答案是不可能正確的。如果問題本身根源於某些錯誤,那麼一切答案都是無濟於事的,而且它們會把你帶進更荒謬的問題中去。它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哲學家就是這樣變瘋的。他們不是去看問題本身的錯誤,而是創造出一個答案;然後這個答案就創造出更多的問題。答案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那麼怎麼辦呢?禪怎麼說?禪說:看一看問題本身,那兒隱藏著答案。深入地看問題,如果看是完美的,那麼問題就會消失。沒有問題是被解答的,它只是消失了;當它消失時,它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在說:問題在哪兒?我們也吃飯,我們也穿衣服,但是我們僅僅吃飯、穿衣服。何必創造問題?睦州在說:生活原本是怎麼樣的,就怎麼樣接受它。不要創造問題。一個人必須吃——那麼就吃。有饑餓,你並沒有創造它,它必須被滿足——那麼就滿足它。可是不要創造問題。
當人們到我這兒來時,就是這樣的情況,天天如此。他們帶來他們的問題,但是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問題,因為本來就沒有問題。你創造了問題,然後你想要它們的答案。有些人會給你答案,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教導;有些人會給你洞見以穿透你的問題,那才是偉大的教導。微不足道的教導導致你墨守成規,而偉大的教導讓你變得放鬆而自然。
睦州說:我們穿衣服、我們吃飯。但是那個人不理解。當然,這麼簡單的事是難以理解的。人們能夠理解複雜的事物,但他們不能理解簡單的事物。因為複雜的事物可以被剖開,分析,用邏輯的方法對付,而對簡單的事物怎麼辦好呢?你不能分析它,你不能斬碎它,你不能分解它——沒有東西可以分解。它太簡單了。而且正因為它是這麼簡單,你會錯過它。那個人不能理解。但我仍然覺得那個人是真誠的,因為他說:我不明白。
有一些很複雜的人會點點頭表示他們明白了。這些人是大傻瓜:沒有人能幫助他們;因為他們老是裝作自己已經懂了。他們不能說他們不明白。如果他們這樣說,他們會自以為很愚蠢。他們裝模作樣。他們怎麼可能不明白這麼簡單的事?他們連續表現出他們已經懂了,現在,更複雜的事產生了。首先,問題不存在,然而,他們卻已經理解答案!問題不存在,而現在他們卻得到了有關問題的知識:他們說他們懂了!他們使自己變得越來越迷惑,裏面亂七八糟。這樣的人到我這兒來,我能看到他們裏面——他們只不過是一團糟的大雜燴。他們什麼也沒明白,他們甚至連他們的問題是什麼都不明白,卻已經擁有了答案。不僅如此,他們還開始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那個人一定很真誠。他說:「我不明白。」這是邁向理解的很好的一步。如果你不明白,你能夠明白;可能性是打開的。你很謙虛,你認識到了困難,你認識到你是無知的,這是通向知道、通向理解的第一步:認識到你不明白。至少他明白了這麼多。這是了不起的一步。
睦州答到:如果你不明白,那麼就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飯。
睦州看上去冷酷無情,但其實不是。他在說:你不能理解,因為頭腦是從來不能理解,頭腦是一個最大的不理解者,是無知的根源。為什麼頭腦不能理解?因為頭腦只是你的存在的一小部分,而部分是不能理解的,只有整體才能夠理解。永遠記住這個:只有你整個的存在才能理解某些東西,部分是不能夠理解的。你的頭不能,你的心也不能,你的手不能,你的腳也不能——只有你整個的存在才行。理解是來自於整體的,誤解是來自於部分的。部分往往會誤解,因為部分往往企圖裝作整體;那就是全部的問題。頭腦企圖說它是整體的理解,而事實上它僅僅是一個部分。
當你進入夢鄉,你的頭腦在哪兒?沒有它,身體照常工作。身體消化食物;沒有必要有頭腦。即使你的大腦被完全取出來,你的身體會照常工作。它會消化食物,它會成長,它會把廢物排出體外。現在,科學家已開始感到頭腦是一個奢侈品。身體有它自己的智慧,它和頭腦無關。你有沒有觀察到,頭腦老是自以為自己知道得很多,而毫不察覺到身體裏面重要的功能都是在沒有它的情況下發揮作用的?你吃食物,身體並沒用問頭腦如何消化它;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要把食物轉化成血液並不簡單,然而身體卻能轉化它,而且不停地工作。由於涉及到成千上萬個因素,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身體恰如其分地分泌汁液用以消化食物。然後它吸收身體需要的東西,把不需要的東西留下,接著將不需要的東西排泄出去。在身體裏,每一秒鐘,成千上萬的細胞在死去,身體不停地把它們排除血液。對荷爾蒙、維生素及其別的東西的需求是難以計數的,而身體總是能從環境中找到它們。當身體需要更多的氧氣時,它就作深呼吸。當身體不需要時,它就放鬆呼吸。一切井井有條——頭腦只是這整個機制中的一部分,而且並不是主要的。不帶有頭腦的動物存在著,樹存在著,而且優美地存在著。然而頭腦是個徹頭徹尾的偽裝者。它只是裝出它是地基,是基礎,是巔峰,是高潮。它一直偽裝著。只要看看你的頭腦,你就會明白。你想靠這個偽裝者來理解嗎?它是你裏面唯一的不老實的東西。
睦州在說什麼?他說:「如果你不明白,那麼就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飯。」不要為理解而煩惱。你就和我們一樣——吃和穿,不要試圖去理解。這個努力本身,這個理解的傾向,就會創造誤解。沒有必要。只是生活和存在。那就是睦州所說的:吃,穿,只是存在。忘掉理解,何必理解呢?如果整個存在不要理解而都存在著,那麼你又何必煩惱呢?為什麼要把這個小小的頭腦攪和進來而自尋煩惱呢?放鬆點,只是存在。
睦州在說,理解來自整體。你只是吃,不要試圖去理解。你只是活動,行走,戀愛,睡覺,吃飯,洗澡。全然地存在。任事情發生。只是存在。不要試圖去理解,因為這個試圖的努力,這個去理解的努力,創造了一個問題。你變得分裂了。不要創造問題——只是存在。
有朝一日,試試這個技巧。我希望你試試這個:有朝一日,到山裏去,3個星期,僅僅存在。不要試圖去理解任何事情——只是存在,自然而放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不想吃的時候,就不吃。沒有強求。把一切事情都留給身體,留給整體。頭腦只是個問題的創造者。有時候身體需要食物時,它說:禁食。有時候身體說:夠了,等一下,不要再強迫任何東西了,它卻說:多吃點,這東西很好吃!——你不在聽整體的話。整體是明智的。再那個整體中你的頭腦、你的身體,一切都是包括其中的。
我並不是說要把頭腦砍掉——那也是不自然的,它也是一部分。頭腦得有屬於自己的位置,屬於自己的比例,但不能允許它成為獨裁者。如果它成為獨裁者,它就會造出問題。然後它尋求解答,而解答又創造更多的問題,你沒完沒了,直到最後進瘋人院。
頭腦的歸宿是瘋人院。走得快的人,當然到得早;走得慢的人,稍晚些到——但是每個人都是排在隊伍裏的。頭腦的歸宿是瘋人院,因為一個試圖去裝成整體的部分早就是瘋了的,狂了的。
所有的宗教都幫著在你的內在創造分裂。所有的宗教都幫助頭腦變得越來越專制。他們說:把身體殺了。而你是不明白自己在幹什麼的,於是你就開始殺死身體。頭腦、身體、靈魂——它們一起存在於一個整體中。它們是一體性的。不要切分;切分是錯誤的,切分是有政治陰謀的。如果你切分,頭腦便成為獨裁者,因為頭腦是身體中最能說會道的部分,它沒別的本事。
生活中也發生同樣的事:如果一個人口才出眾,他將成為眾人的領導。如果他伶牙俐齒,如果他是個雄辯家,如果他巧於言辭,他將成為領導。並不是他有能力成為領導,而是因為他是健談的人,給人們的頭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個出色的說服者,優秀的推銷員,能說會道。那就是為什麼雄辯家領導著世界。當然,他們將世界領入越來越深的混亂,因為他們不是眾人的領導。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他們別無所長。因此你們的國會僅僅是談話的房子。人們不停地說話,誰口齒伶俐,誰就成為首領。那就是為什麼你們的國會和瘋人院沒什麼兩樣——他們是一回事。
整體存在的品質是完全不同的。這不是能言善辯的問題,而是如何安排每一個部分的問題,它是一種和諧。它給予你的生命一種和諧的節奏,每一部分都在它的裏面存在。這樣,頭腦也是美麗的。它不再帶你進入瘋人院。它將變成偉大的頭腦,它將開悟。但你的整體完整地存在;你不分割你自己;你的智慧仍然是完整的。那正是睦州的意思,那正是禪的整個努力。
那就是為什麼我說禪是一種罕見的現象。沒用別的宗教能夠達到這麼偉大的開花。因為禪認識到了理解是來自於整體的——你吃,你睡,你是很自然的,你就是整體的,而不要試圖分割你自己,分割頭腦和身體,分割靈魂和物質。不要分割。伴隨分割而來的是衝突和暴力,伴隨分割而來的是無數的問題,而且沒有解決的方法。或者說,只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那就是再一次成為整體,把一切都留給自然的整體。
頭腦仍然存在,可是它的作用將完全不同。我也用我的頭腦。我正在和你們說話,頭腦是需要的。為了交流,頭腦是需要的;事實上,它是一個交流工具。為了記憶,頭腦是需要的。它是一台電腦。但為了存在,你的整體是需要的。在身體裏——當我說「身體」時,我是指你的整體:身體,頭腦,靈魂——每個部分各有各的作用。如果我想抓住什麼東西,我將用我的手。如果我想移動,我將用我的腿。如果我想交流,我將用我的頭腦。僅此而已。也就是說,我保持整體狀態。當我使用雙手時,我的整體支援我的雙手。它們並不和整體對著幹,而是和整體合作。當我使用雙腿走時,是整體在協調中使用它們。事實上,它們在為整體發揮作用,為整體行走,而不是為它們自己。如果我和你談話、交流,我為整體而使用頭腦。如果我的整個存在中的某些東西希望我交流,我就使用我的頭腦,我就使用我的雙手和我的表情,我就使用我的雙眼;但是它們是為整體使用的。整體仍然是最高的,整體是主人。當部分成為主人,你就會分裂,你的一體性就會喪失。
睦州說:如果你不明白,何必明白。不要為此擔憂。你就回去,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飯。我不知道那人以後是怎麼做的,但是對你們我也要說:如果你明白——棒極了。如果你不明白——走吧,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飯。因為理解會成為你整體存在的陰影。在生命的整體中活。不要害怕完整的生活。不要做一個懦夫,不要試圖逃離到山野和寺廟中去。
我已經教給你們在這個世界上盡可能完整地生活的桑雅世。只要全然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就會超越它。你會突然知道你在這個世界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帶給了你們關於桑雅世的全新的概念。舊的桑雅世的意思是:逃離,放棄!可是我告訴你那些逃離的人是懦夫,我告訴你那些逃離的人不是整體,不是全然的。我告訴你那些逃離的人是殘廢的。這對你是不合適的。你在生命的整體中生活,你生活,盡可能地全然地生活。你越是活得全然,你就變得越神聖。當一個人勇敢地生活,沒有恐懼,沒有希望,沒有欲望時,神聖的品質就會降臨。這個人只是從一個片刻滑入下一個片刻,完全是新鮮而嶄新的。
這就是對你們來說桑雅世的含義。桑雅世就是生活在生命的全然中,從一個片刻到另一個片刻;允許它毫無條件地發生在你的任何部分。然後,如果你能允許這麼多,生命就會允許你超越。保持在山谷裏,你就會成為山峰,只有那時它才是美麗的。如果你走向山峰,山谷就丟失了——山谷有它自身的美。如果你停留在山谷裏,山峰就丟失了——山峰有其自身的美。我希望你成為山谷山峰之人,喝二為一。保持在山谷裏卻成為山峰——然後你就能夠理解禪是什麼。
摘錄自「春來草自青」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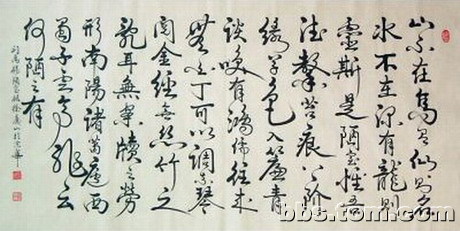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