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面目
 一群憤怒的和尚由惠明帶領追逐逃跑的慧能,後者已經遵循五祖的勸告,暗地離開了寺院。當他要越過一個大庾嶺的山道之際,惠明等人趕了上來;慧能把衣缽放在附近的石頭上,對惠明和尚說:「這件法衣,代表著我們的信仰,不是武力所可爭奪的,如果你要,可以取去。」
一群憤怒的和尚由惠明帶領追逐逃跑的慧能,後者已經遵循五祖的勸告,暗地離開了寺院。當他要越過一個大庾嶺的山道之際,惠明等人趕了上來;慧能把衣缽放在附近的石頭上,對惠明和尚說:「這件法衣,代表著我們的信仰,不是武力所可爭奪的,如果你要,可以取去。」
惠明去取,但法衣重得如山一般。他住手,猶豫,因敬畏而顫抖,終於他說:「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望行者為我掃除愚昧。」
六祖說:「你既然是為法來,請把一切心念,不思善不思惡,看看你未生以前的面目是什麼。」(「不思善,不思惡,正于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經這樣一提,惠明立即悟得了一切事物的根本,而這是他一直尋求卻尋求不到的。現在他之瞭解一切,就如同飲了一杯冷水,感受到它們的沁涼。由於強烈的感動,他汗淚並流,恭敬的走近六祖,行禮說道:「除了這深遠的話中所含的意義之外,還有其他奧秘的東西嗎?」
六祖回答說:「我所指明的事物中沒有隱藏的東西。如果你反觀內在,你會認出你的本來面目,這本來面目是有世界之前即已有的;奧秘在你心中。」.....
臨濟宗的創始人臨濟義玄有一次就這般說:「各位求道者,你們不要以為佛是無上完滿者。在我看來,他不過是一個糞池。菩薩與尊者──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枷鎖你的器具。因此,文殊劍殺瞿雲,而鴦掘(Angulimala)刀傷釋迦。各位修道者,沒有什麼佛道可得的。所謂「三乘」,「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性」,「圓頓」之教等等──所有這些都只是用來治療種種疾病的方法;它們本身是沒有實質的。不論它們自稱具有何等實質,都只不過是象徵性的表現,除了文字的戲論之外無他。
「各位修道者,有些禿子想抓住某種東西做依附,以便可以讓他們解脫世俗的枷鎖。大錯,求佛失佛,求道失道,求祖失祖。」(譯注:見《臨濟錄》)
如此看來,禪師們在傳道工作中,所要做的顯然是儘量使弟子有獨立性與原創性,不僅是對傳統佛教的解釋上為然,在他們自己的思想方式上亦然。如果有什麼事情可說得上是讓他們十分厭惡的,那就是對於外在權威的盲目接受,以及對於因循習俗的謙卑屈從。
他們要求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個體性和靈性。他們給予心靈完全的自由,任其自我展現;這種心靈的自我展現是不可以被任何人為的事物去阻礙的──諸如把佛當作救世主來崇拜,對於經典的盲目信從,或對於任何外在的權威之無條件的依傍。
他們告誡弟子,不論任何事物,必得由他們自己證實為真,才可接受。一切事物,不論是神聖的或凡俗的,都要加以摒棄,因為它們不屬於自心。他們說,不可執著於感覺,不可執著于理智,不可依傍二元論,不可依傍一元論,不可被某種絕對體所誘,不可被神所誘,你只要是你自己,則你將虛如太空,自由如空中鳥或水中魚,你的精神將明澈如鏡。佛與非佛,神或非神,這一切只不過是遁詞,是文字遊戲,沒有真實的意義。
這是我從鈴木大拙的"禪學隨筆"中"佛教中的禪宗"摘錄下來的。六祖和臨濟義玄所說的,是我一直在想也一直在找的。被我用粗體加強的字句,也正是我想用來告訴我自己和周圍的朋友的。
自性是什麼?自性在哪裡?我是什麼樣子?除了我自己,有誰能給我答案?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我現在不做什麼,不代表我以後都不會做。現階段對我來說,清楚自己,遠比對外做什麼要重要的多。有幾位朋友對我目前的獨善其身和一些避世作法不以為然,用一些軟硬方式,想讓我有一些行動,做一些事。
朋友看得起我,認為我有能力為社區做一些事。只是,在不同的生命過程,有時也真的需要有一些轉換和休息。我清楚知道這不過是個過程,沈澱讓我更有空間和時間,去思考人生的意義和我未來的方向,讓我再次出發時,能有更有效,更觸動的做法及分享。
老實講,不管是我要求朋友做什麼或不要做什麼,或朋友期待我,要求我做什麼,都是比較不切實際的,決定權都還是在別人手上;只能建議,不能強求。倒不如回到自己身上,清楚自己要什麼,能做什麼;用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呈現自己的樣子,那會是更適當的吧!
兩則故事
敬鐘如佛
鐘,是佛教叢林寺院裏的號令,清晨的鐘聲是先急後緩,警醒大眾,長夜已過,勿再放逸沈睡。而夜晚的鐘聲是先緩後急,提醒大眾覺昏衢,疏昏昧!故叢林的一天作息,是始於鐘聲,止於鐘聲。
有一天,奕尚禪師從禪定中起來時,剛好傳來陣陣悠揚的鐘聲,禪師特別專注的豎起心耳聆聽,待鐘聲一停,忍不住的召喚侍者,詢問道:「早晨司鐘的人是誰?」
侍者回答道:「是一個新來參學的沙彌。」
於是奕尚禪師就要侍者將這沙彌叫來,問道:「你今天早晨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在司鐘呢?」
沙彌不知禪師為什麼要這麼問他,他回答道:「沒有什麼特別心情!只為打鐘而打鐘而已。」
奕尚禪師道:「不見得吧?你在打鐘時,心裡一定念著些什麼?因為我今天聽到的鐘聲,是非常高貴響亮的聲音,那是正心誠意的人,才會發出這種聲音。」
沙彌想了又想,然後說道:「報告禪師!其實也沒有刻意念著,只是我尚未出家參學時,家師時常告誡我,打鐘的時候應該要想到鐘即是佛,必須要虔誠、齋戒,敬鐘如佛,用如如入定的禪心,和用禮拜之心來司鐘。」
奕尚禪師聽了非常滿意,再三的提醒道:「往後處理事務時,不可以忘記,都要保有今天早上司鐘的禪心。」
這位沙彌從童年起,養成恭謹的習慣,不但司鐘,做任何事,動任何念,一直記著剃度師和奕尚禪師的開示,保持司鐘的禪心,他就是後來的森田悟由禪師。
奕尚禪師不但識人,而從鐘聲裏能聽出一個人的品德,這也由於自己是有禪心的人。諺云:「有志沒志,就看燒火掃地」,「從小一看,到老一半」。森田沙彌雖小,連司鐘時都曉得敬鐘如佛的禪心,難怪長大之後,成為一位禪匠!可見凡事帶幾分禪心,何事不成?
對事對物要帶禪心,對人呢?
凡聖兩忘
南塔光涌禪師初參仰山禪師時,仰山問他:「你來做什麼?」
光涌答:「來拜見禪師。」 仰山又問:「見到了禪師嗎?」
光涌答:「見到了!」
仰山再問:「禪師的樣子像不像驢馬?」
光涌說:「我看禪師也不像佛!」
仰山不放鬆再追問:「既不像佛,那麼像什麼?」
光涌則不甘示弱地回答:「若有所像,與驢馬有何分別?」
光涌大為驚嘆,說道:「凡聖兩忘,情盡體露,二十年之中,再也無人優勝於你,你好好保重。」
事後仰山禪師一見到人就讚歎說:「光涌為肉身佛也。」
這則公案究竟有何含意呢,譬如有人問人像什麼?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假如有所像,就有所不像。如果回答說人像鬼,鬼中也有人;如果說鬼像人,人中也有鬼。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虛空像什麼?虛空無相無所不相,正因為虛空無相,才能包容萬有;虛空無相,所以像一切的樣子。仰山禪師和光涌禪師議論不像驢,不像佛,那麼究竟像什麼?像自己。唯有見到自己的自性,才能與虛空一個鼻孔出氣,像什麼?像虛空無相之相。能夠凡聖兩忘,體用一如,那就是見到無相的真理了。
朋友們對我有一些期待,他(她)們腦中有一些我該是的樣子。但我究竟是什麼樣?什麼是我的本然?能被說出來,就已不完全。我自己都不完全清楚,他(她)們又如何能全知?也許他(她)們看到了什麼,可以成為我對自己認識的參考,但又怎知那不是他(她)們自己內在的投射?
我要怎麼做?可以怎麼做?不是為做而做,不是為滿足別人期待而做,也不要為了不想變成別人想要的樣子而不做,而是真正成為自己,發揮自己;那是我需要好好思考和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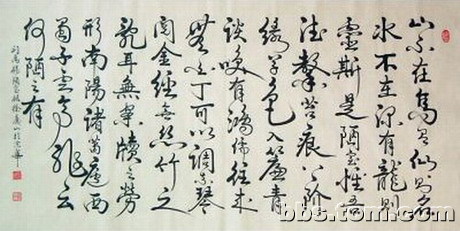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