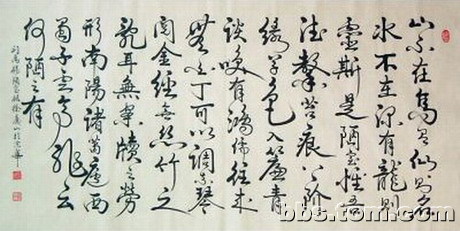英國某小鎮有一個青年人,整日以沿街為小鎮的人說唱為生;
英國某小鎮有一個青年人,整日以沿街為小鎮的人說唱為生;
這兒,有一個華人婦女,遠離家人,在這兒打工。
他們總是在同一個小餐館用餐,於是他們屢屢相遇。時間長了,彼此已十分的熟悉。
有一日,我們的女同胞,關切地對那個小夥子說:
「不要沿街賣唱了,去做一個正當的職業吧。我介紹你到中國去教書,在那兒,你完全可以拿到比你現在高得多的薪水。」
小夥子聽後,先是一愣,然後反問道:
「難道我現在從事的不是正當的職業嗎?我喜歡這個職業,它給我,也給其他人帶來歡樂。有什麼不好?我何必要遠渡重洋,拋棄親人,拋棄家園,去做我並不喜歡的工作?」
鄰桌的英國人,無論老人孩子,也都為之愕然。他們不明白,僅僅為了多掙幾張鈔票,拋棄家人,遠離幸福,有什麼可以值得羡慕的。
在他們的眼中,家人團聚,平平安安,才是最大的幸福。它與財富的多少,地位的貴賤無關。於是,小鎮上的人,開始可憐我們的女同胞了。
中國山東,有這樣一對夫婦剛剛結婚時,妻子在濟甯,丈夫在棗莊;過了若干年,妻子調到了棗莊,丈夫卻一紙調令到了菏澤。棗莊,若干年後,妻子又費盡周折,調到了菏澤。但不久,丈夫又被提拔到了省城濟南。妻子又托關係找熟人,好不容易調到了濟南。可是不到一年,丈夫又被國家電業總公司調到重慶。於是,她所有的朋友,就給她開玩笑--你們倆呀,天生就是牛郎織女的命。要我們說呀,你也別追了,乾脆辭職,跟著你們家老張算了。
但是,她以及公婆、父母,都一致反對。幹了這麼多年,馬上就退休了,再說,你的單位效益這麼好,辭職多可惜。要丟掉多少錢呀!再幹幾年吧,也給孩子多掙一些。其實,他們家的經濟條件已經非常優越。早已是中層階級,但是他們仍然惦念著那一點退休金。於是,夫妻兩個至今依然是牛郎織女。
我們,是一個尚義輕利的民族(不見得吧,有些往自己臉上貼金)。中國人一直是為了某種自己未必真正明白的主義而活著。於是,中國人,不能在沒有目標的生活中活著。而這個目標,可以是工作,可以是理想,可以是金錢,可以是孩子,可以是老人……但是,唯一不可能是的,就是自己。
中國人,可以很委屈的活著。可以是工作上的極不順心,可以是婚姻上的勉強維持,可以是人際關係上的強作笑顏,可以是所有欲望的極端壓制,可以是為了一個所謂的戶口 ……哪怕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在所不惜。
中國人,可以過異常艱難的日子,但並不能安貧樂道,他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必定有一個近乎玩笑的藉口;中國人,可以把高官厚祿當作成功,中國人可以把身家百萬當作理想,中國人可以拋卻天倫之樂,四海飄蕩,但是,中國人唯一不認可的成功——就是家庭的和睦,人生的平淡。
於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把愛國、崇高、獻身、成功、立業的情結推向了極致——他們要麼在大公無私,其實是捨本逐末的漩渦痛苦掙扎,要麼在肩負重任,其實是徒有其名的圈圈受盡折磨。
……唯一遺漏的就是自由和自我。於是,在外國,婦孺皆知的道理;在中國,沒人能整治明白。
人的一生,到底在追求甚麼?
有一個美國商人坐在墨西哥海邊一個小漁村的碼頭上,看著一個墨西哥漁夫划著一艘小船靠岸。小船上有好幾尾大黃鰭鮪魚,這個美國商人對墨西哥漁夫能抓這麼高檔的魚恭維了一番,還問要多少時間才能抓這麼多?
墨西哥漁夫說,「才一會兒功夫就抓到了。」
美國人再問,「為甚麼不待久一點,好多抓一些魚?」
墨西哥漁夫覺得不以為然 :「這些魚已經足夠我一家人生活所需啦!」
美國人又問:「那麼你一天剩下那麼多時間都在幹甚麼?」
墨西哥漁夫解釋:「我呀?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幾條魚,回來後跟孩子們玩一玩;再跟老婆睡個午覺,黃昏時晃到村子喝點小酒,跟哥兒們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過得充滿又忙碌呢」
美國人不以為然,幫他出主意,他說:「我是美國哈佛大學企管碩士,我倒是可以幫你忙!你應該每天多花一些時間去抓魚,到時候你就有錢去買條大一點的船。自然你就可以抓更多魚,在買更多漁船。然後你就可以擁有一個漁船隊。到時候你就不必把魚賣給魚販子,而是直接賣給加工廠。然後你可以自己開一家罐頭工廠。如此你就可以控制整個生產、加工處理和行銷。然後你可以離開這個小漁村,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磯,最後到紐約,在那經營你不斷擴充的企業。」
墨西哥漁夫問:「這又花多少時間呢?」
美國人回答:「十五到二十年。」
墨西哥漁夫問:「然後呢?」
美國人大笑著說:「然後你就可以在家當皇帝啦!時機一到,你就可以宣佈股票上市,把你的公司股份賣給投資大眾;到時候你就發啦!你可以幾億幾億地賺!」
墨西哥漁夫問:「然後呢 ?」
美國人說:「到那個時候你就可以退休啦!你可以搬到海邊的小漁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隨便抓幾條魚,跟孩子們玩一玩,再跟老婆睡個午覺,黃昏時,晃到村子喝小酒,跟哥兒們玩玩吉他 !」
墨西哥漁夫疑惑的說:「我現在不就是這樣了嗎?」
人的一生,到底在追求甚麼?
 諂笑柔色應酬,人間才有華彩;唯有著誠去偽,
諂笑柔色應酬,人間才有華彩;唯有著誠去偽,